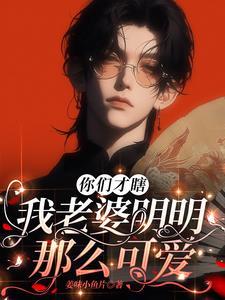顶点文学>灶神的味觉:庶女厨娘逆袭录 > 第442章 旧厨重现真心之味(第1页)
第442章 旧厨重现真心之味(第1页)
苏小棠的指尖在灶台上凝住了。
灶膛余烬的温度透过粗粝的草灰渗进掌心,和十二岁那年的冬夜一模一样。
那时她蹲在灶前扇火,冻得通红的手总被火星子燎到,是陆明渊突然俯身替她握住蒲扇,说"笨手笨脚",扇风的力道却轻得像怕惊飞灶王爷。
可此刻,灶边站着的不是陆明渊,是系着靛蓝围裙的妇人——她的母亲,在她十四岁那年染了风寒,连最后一口热粥都没喝上就咽了气的母亲。
"小棠?"妇人舀水的手顿住,转身时银簪在旧光里晃了晃。
她眼角有细纹,围裙前襟沾着几点面渣,和苏小棠藏在箱底的旧绣像上的模样分毫不差。"什么呆呢?"妇人擦了擦手走过来,粗糙的指腹蹭过她冻红的鼻尖,"灶上温着姜茶,先喝两口暖暖。"
苏小棠的喉咙突然哽住。
她记得这双手,记得母亲临终前摸她脸时的温度,像被抽干了所有热气的枯枝。
可此刻这双手带着灶房的烟火气,带着新揉好的面团的绵软,带着她十二岁那年所有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依恋。
"阿娘"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抬手去碰那双手,却在将触未触时顿住——指尖悬在半空,像生怕碰碎了这层幻觉。
"傻丫头。"妇人笑了,拉着她的手按在自己手背上,"阿娘的手糙,可暖着呢。"
苏小棠的眼泪"啪嗒"砸在两人交叠的手背上。
三年了,她在侯府洗衣房被热水烫红的手没人揉,在御膳房被刀背抽肿的胳膊没人问,连本味感知作时疼得蜷成虾米,都只能咬着帕子忍。
可此刻,这双带着面香的手正轻轻替她揉着虎口,像她小时候摔了碗被嬷嬷骂,母亲偷偷带她躲进这小厨房时那样。
"姐姐!"
稚嫩的喊声从门口传来。
苏小棠猛地转头,看见个扎着双髻的小丫头扒着门框,灰扑扑的粗布裙角沾着草屑,眼睛亮得像缀了星子。
那是十二岁的她自己,刚被嫡姐沈婉柔罚去扫马厩,回来时顶还沾着草叶,却巴巴地凑过来,"我闻见糖糕香了!"
幼年苏小棠的声音撞进耳膜的刹那,苏小棠的太阳穴突突地跳。
她想起被沈婉柔推下井的那个雨夜,想起被扔进柴房三天没饭吃时,自己偷偷摸进这小厨房,用最后半块红糖和着偷来的糯米粉蒸糖糕——那是她第一次用本味感知,也是第一次尝到"甜"的滋味,不是糖的甜,是"活着"的甜。
"姐姐给你做。"苏小棠听见自己说。
她转身走向案板,手指刚触到竹筐里的糯米粉,记忆便如潮水涌来:母亲站在她身侧,教她"水要分次加,揉面要像哄娃娃";幼年的自己趴在案边,数着她撒的桂花,说"要撒九颗,九是最大的数";灶火舔着锅底,蒸汽模糊了窗纸,却模糊不了那句"小棠做的糖糕,比宫里的点心还甜"。
糯米粉在掌心成团的触感让她鼻尖酸。
她突然明白苏清澜说的"最真实的味道"是什么——不是御膳房里用金铲银勺炒出的珍馐,不是天膳阁里让达官贵人惊叹的创新菜,是这小厨房里,用粗陶碗装着、沾着灶灰、带着她和阿娘体温的糖糕。
是她十二岁时就明白的事:烹饪不是为了讨好谁,是为了把"活着"的滋味,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阿娘帮你烧火。"妇人已经蹲在灶前,用蒲扇轻轻扇着余烬。
火星子噼啪跳起,映得她眼角的细纹都泛着暖光。
幼年苏小棠搬了个矮凳凑过来,下巴搁在案上看她包糖馅:"姐姐要包月牙形的,我喜欢月牙。"
"好,月牙形。"苏小棠的手指翻飞,糯米皮裹着红糖芝麻馅,在掌心团成月牙模样。
她想起第一次包糖糕时,手笨得总把皮捏破,是母亲握着她的手说"别急,慢慢来,甜的东西,值得等"。
蒸笼搁上灶台时,蒸汽"噗"地冲起,模糊了眼前的景象。
苏小棠望着腾起的白雾,突然看清了舌尖之战的真相——这关考的从来不是刀工火候,是她还记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拿起这把菜刀。
"要熟了。"母亲的声音从雾气里传来。
幼年苏小棠扒着蒸笼边,鼻尖都快贴到竹篾上了:"姐姐我要吃最大的那个!"
苏小棠笑着应下,手却在掀蒸笼的瞬间顿住——蒸汽散尽的刹那,她看清了笼里的糖糕:月牙形的皮面微微裂开,露出内里红褐色的糖馅,甜香混着桂花香漫出来,和十二岁那年的糖糕分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