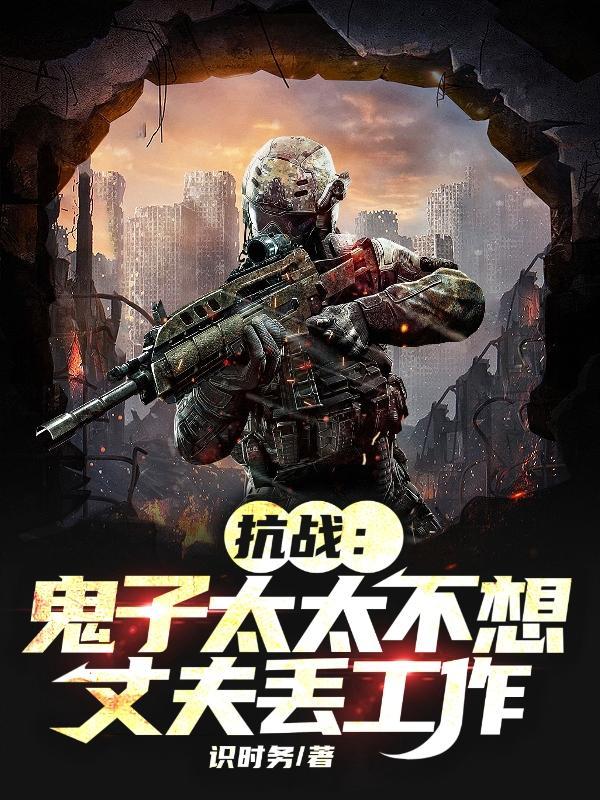顶点文学>玻璃情话 > Sandm 12(第3页)
Sandm 12(第3页)
捂住嘴,哑然失声。
^
都在同一个学校,平时训练又是同一间的舞蹈教室,林弥初或多或少都清楚大家的水平大概在哪。
但即使是这样,她也没松懈下所有的基本训练。即使是做自己擅长的事,她也要全力以赴。
比赛那天台北下了很大的雨,原先定好的室外舞台被挪到了室内。
本来可以允许学生旁观的席位也被取消,只剩下没几个位置。
那天讲来并没有什麽稀奇的地方,寂静的比赛场地和舞蹈教室也没有什麽区别,除了多出坐在场下的那三双审视的眼睛。
林弥初跳的时候耳边里只剩下水声,滴滴答答地掉,分不清是额头掉落的汗还是伴奏。
密闭空间里映出的影子也是潮湿的,细灰尘被日光映白,呼吸雨了又晴。
她站在聚光灯下,每次擡高的修长手臂和扬起的发丝都像是被打湿仍然奋力起飞的蝴蝶。
蓝色的丶缄默的丶充满感染力的。
没有失误。
一次也没有。
是林弥初跳舞生涯里最完满的一次。
然而颁发奖状的时候,评委并没有把名次如愿给她,而是给了徐临雨。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的不公,但是谁也没有站出来说。
她拿着与第一名失之交臂的奖状,站在镜头最外侧合影,连一个笑都没有。
回去路上路过隔壁教室。
听到半开的教室门边传来一道神气的嗓音,徐临雨被簇拥着翻看第一名奖状,讥讽地说:“即便重来一次,第一名也还会是我。”
“只要我想要。”
林弥初拿着奖状的那只手突然没了力气。
她往回跑,不顾一切地往回跑,一头扎进舞蹈教室,整个人跪倒在地面。
她想到自己被迫开始跳舞的那几年的“不和谐”,因为经济能力走不通的前路,想要的丶差一点就能够到的电影票。
多年辛苦付之一炬。
压抑许久的委屈排山倒海把她淹没。
排练的落地镜映出她发涩的眼睛,眼泪掉到手背和被攥得发皱的奖状上。
这一刻,她忽然有些辨不清这麽多个咬牙努力的日夜究竟是为了什麽,练习时浑身上下滚出的淤青又算什麽。
背後的门把手被人拧开,眼前扎进一双黑色帆布鞋。
林弥初哭得没劲的手臂被人一把拉起,眼泪再无处可藏。
她很少哭。
哪怕是最先开始跟不上的那些基础课和後来难以为继的学费,也从没让她认输掉过眼泪。
柯叙凛沉默蹲在她的跟前,握住她跪得发疼的膝盖,接着摁着她的眼角,把她的眼泪全部擦干净。
他说:“你还想继续跳舞吗?”
“只要你说想,我供着你上。”
林弥初流着泪给了他一下:“你有病啊,柯叙凛,你哪来的钱?”
“我可以挣,”他被打了反而笑,顺势和她一块坐下来,“你只要说想不想。”
那道认真的视线落到眼睛里,是和香烟灰一样令人心悸的滚烫。
他没在开玩笑。
就和小时候说过要让她学会骑单车一样,说到做到。
林弥初擦干眼泪,偏过头,说不想。
“我可以走别的路,走的也不会比现在差。”
她林弥初,就算一切从头,也能硬生生闯出一条路来。
柯叙凛睨着她,笑得又痞又浑。
他没再说别的,只轻轻说了四个字,人定胜天。
这四个字在这之後,几乎印进了林弥初的生命里。
就算是命中早就注定。
你也依然有挑战命运,直到战胜它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