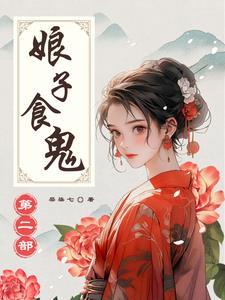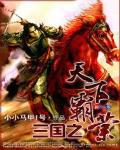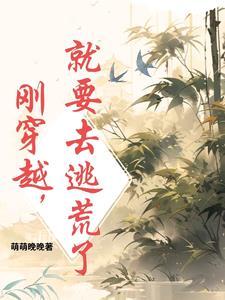顶点文学>我想声色犬马,你叫朕当千古一帝? > 第30章 更改科举制度天下寒门皆可登堂(第1页)
第30章 更改科举制度天下寒门皆可登堂(第1页)
算学!军略!这才是治国安邦的实学啊!”
“陛下圣明!陛下万岁!”
……
数日后,恩科开考之日,京城贡院之外,景象蔚为壮观。
往日科考,贡院门口多是锦衣华服、仆从簇拥的世家子弟,或是略显寒酸却也书卷气十足的儒生。
然而今日,这里却被另一番景象所占据。
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一眼望去,竟多是些穿着粗布短打、面带风霜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些胡须花白、身板硬朗的老者。
他们不像传统考生那般手捧《四书》《五经》,而是攥着一把把磨得光滑的算筹,或是小心翼翼地捧着几卷纸张泛黄、墨迹淋漓的兵书策论。
周元庭换上了一身寻常监考官的青色官服,隐在人群中观察。
这些面孔,与金銮殿上那些养尊处优、世故圆滑的官员截然不同,充满了未经雕琢的生机与渴望。
他的脚步停在了一个角落。
一个看上去年纪不过十六七岁的少年,正蹲在地上,面前铺开一张粗糙的草纸,手指飞快地拨动着一把小巧的算筹。
纸上画着歪歪扭扭的图形,标注着一些数字和符号。
少年眉头紧锁,嘴里念念有词:“引水渠宽三尺,深两尺,坡度……日夜可灌田五十亩……若遇旱年,蓄水塘容量……”
周元庭微微颔首。
这少年推演的,赫然是一种“亩产百斤良田灌溉法”的优化方案。
虽然稚嫩,但思路清晰,注重实效,远非那些空谈仁义道德的腐儒可比。
他又踱步到另一边,只见一个面带沧桑、断了一指的中年汉子,正摊开一卷写满了字的旧布,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关于骑兵粮草转运的计策。
此人看穿着打扮,应是行伍出身的退伍兵士。
周元庭凑近细看,那布上所书,皆是此人戍边多年的亲身见闻与总结,名曰《骑兵粮草转运十策》,其中不乏利用沿途驿站、民夫、乃至敌占区资源的奇思妙想,极具操作性。
“此二人,可有户籍凭证?”周元庭侧头,低声问身边一名负责登记的礼部小吏。
小吏翻了翻名册,面露难色:“回……回大人,这二人皆是流民,并无在册户籍,按例……不得入场。”
“按例?”周元庭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传朕旨意,今日恩科,但凡能通过算学、军略初试者,无论有无户籍,一律准许入场!”
“啊?这……这不合规矩啊,陛下!”小吏大惊失色。
周元庭眼神一厉:“朕的话,就是规矩!”
小吏吓得一个哆嗦,不敢再言,连忙跑去传达命令。
消息一出,贡院外顿时一片哗然,那些原本因为没有户籍而绝望的寒门子弟,爆发出难以置信的欢呼,不少人当场激动得涕泪横流,朝着皇宫方向连连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