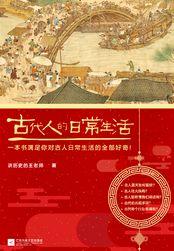顶点文学>女尊:随俗而已,非渣 > 第163章 云暗晋都(第1页)
第163章 云暗晋都(第1页)
天剑江的冰刚化透时,楚羽在淮川郡的水寨里收到了北境斥候的密报——只用了半张纸,字迹潦草得像被风吹过:“武安君已离云州,回晋都。”
他捏着密报站在江滩上,初春的风还带着凉意,卷着江水的潮气往衣领里钻。阿青站在身后,见他半天没说话,忍不住低声问:“先生,张曦突然回去,会不会是……”
“不是好事。”楚羽打断他,指尖在密报边缘捻了捻,纸页被捏出几道褶皱。张曦守北境三年,除非晋都出了天大的事,否则绝不会轻易离开燕云州。何况她走得这样急,连黑风口的马场都没交代妥当——斥候说,李蓉接了令后,正带着骑兵在江对岸焦躁地巡逻,马蹄把燕云州的土都踏松了。
他转身往水寨里走,脚步比来时沉了些。这些年他在大景布防、改革,说到底是想稳住天剑江两岸的平衡,可张曦这一走,平衡怕是要碎了。
“先生要回景都吗?”阿青追上来问。
楚羽没立刻答。他想起安诗妤上次派信使来时,信里夹着的那片干枯的桂花——是景都御花园里的,她大概是想说,都城的花又开了。可现在的他,回得去吗?
三日后,景都典籍署。
楚羽把一本《天剑江水利志》放回书架最顶层,转身时正撞见林晚晴抱着账册进来。她见他收拾了个小包袱放在桌角,愣了愣:“先生这是……要走?”
“嗯。”楚羽点头,声音轻得像怕惊落窗台上的灰尘,“辞官。”
林晚晴手里的账册“啪”地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捡,指尖却抖得厉害:“好好的辞什么官?天剑江的水寨刚修好,淮川郡的新稻种还没推广完……”
“这些事,林尚书和陛下都能办好。”楚羽捡起账册递还给她,目光落在窗外——御花园的方向飘来几片云,遮住了日头,“我留着,反而碍事。”
他没说张曦的事,也没说晋都可能藏着的祸端。有些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林晚晴还想劝,却见楚羽从袖袋里掏出块玉佩放在桌上——是安诗妤当年赐的“镇北侯”令牌,玉上的“侯”字被摩挲得亮。她忽然懂了,楚羽不是一时冲动,是早做了决定。
“我去跟陛下说。”林晚晴捏着账册往外走,脚步有些踉跄。
楚羽看着她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这一走,大景朝堂定会有波澜,可他别无选择。
御书房里,安诗妤听完林晚晴的话,指尖在案上的青瓷镇纸转了半圈,没立刻说话。殿内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鸟鸣,林晚晴站在原地,手心都攥出了汗。
“他留话了吗?”安诗妤忽然问,声音平得听不出情绪。
“留下了侯令,跟一封信。”林晚晴道。
最后安诗妤接过,打开来看:
慌张,是因为准备不足。
急躁,是因为经历不够。
轻浮,是因为磨砺不多。
心乱,是因为思路不清。
压力,是因为期望过高。
贪婪,是因为欲求太满。
心累,是因为想法太多。
劳苦,是因为方法不对。
骄傲,是因为目光短浅。
懒散,是因为目标不明。
暴躁,是因为自身无能。
恐惧,是因为要求过盛。
憎恨,是因为肚量不够。
痛苦,是因为不懂满足。
烦恼,是因为固执追求。
且停且忘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
安诗妤看完过后表面上并没有什么动静只是点点头,拿起镇纸压在刚批阅完的奏折上,淡淡道:“准了。传旨下去,楚羽功成身退,赏黄金百两,良田千亩,不必再入朝觐见。”
林晚晴愣住了——就这么准了?她以为陛下至少会留留他,哪怕假意挽留也好。
“退下吧。”安诗妤没看她,目光落在窗外的宫墙上。
林晚晴躬身退出去,殿门关上时,她听见陛下轻轻说了句什么,声音太低,没听清。
其实安诗妤说的是:“终究还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