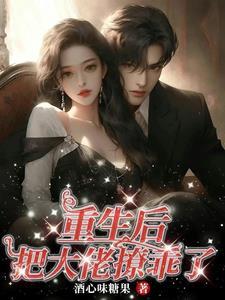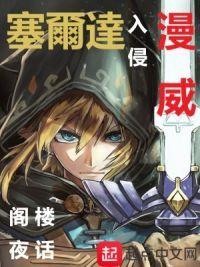顶点文学>大明:入仕从师爷开始 > 第52章 宣府密道(第1页)
第52章 宣府密道(第1页)
腊月初二,宣府城墙箭如雨下。蒙古汗王举着佛郎机炮图纸,狞笑着挥手。
炮口喷出火舌,炮弹却在距城墙十步处炸开。烟尘中,明军箭矢骤雨般反扑,首排骑兵应声倒地。
“怎么回事?!”汗王砸图纸,忽见红旗下闪出严楼身影。他胸前验尸格目翻动,页角标着“错误标尺”四字。
总兵府密室,严楼按住总兵颤抖的肩。案头密信残页上的龙形印记,与他在火器模具所见分毫不差。
“嘉靖三年,您收了兴隆钱庄三千两。”严楼指尖划过对方袖口朱砂渍,“图纸标尺错了三度,您早该知道。”
总兵扑通跪地,指甲抠进砖缝。暗格里滚出的,正是严嵩私铸的龙纹火铳,枪托刻着“乙酉年舞弊”编号。
“开密道!”严楼踹开暗门,冷风卷着雪灌进。三十步外的地道里,神机营士卒顶盔掼甲,炮口对准蒙古后军。
炮声轰鸣中,严楼捡起地道砖缝的孔雀石碎屑。这与贵溪矿脉、嘉靖御墨同源的石头,此刻嵌在砖面龙纹眼里。
京城,嘉靖看着顺天府呈来的铜印,指腹碾过“固皇权”三字。案头严嵩的供状已烧剩半页,独独“蒙古密约”四字清晰。
“传旨,”他盯着窗外落雪,“严楼留任宣府,兼查边将账册。”烛影里,他袖口的半枚龙形玉佩,与案头铜印缺口严丝合缝。
宣府城外,蒙古军帐。汗王盯着染血的图纸,忽然发现标尺数字间,藏着极小的寒鸦暗纹——与严嵩密室残画一致。
“大汗,明军地道!”探马闯入。汗王转身,正见火光从地底窜出,佛郎机炮的轰鸣声响彻草原,却再无一枚炮弹击中城墙。
严楼站在地道尽头,望着石壁新刻的“弘治十七年”。箭头所指处,砖缝里塞着半片带血的黄绫,绣着与女尸相同的银线云纹。
“师父,地道通向东边!”张顺举灯在前。转角处,七具枯骨倚墙而坐,每具腕骨都有龙形疤痕,怀中有卷被虫蛀的《大明会典》。
翻开残页,严楼瞳孔骤缩。弘治朝密道图上,用朱砂圈着的不仅是严嵩私宅,更有京城十二处要害——包括紫禁城的西华门地道。
城外喊杀声渐歇,严楼摸着枯骨腰间的锈蚀腰牌。“弘治朝司礼监暗卫,”他低声道,“二十年前,他们本该护送太子遗诏。”
张顺忽然指着石壁顶端:“师父,寒鸦展翅图!”岩画边缘,用贵溪朱砂描着行小字:“严嵩之后,还有‘严’字”。
夜风卷着雪灌进地道,严楼忽然听见头顶传来砖石挪动声。抬头望去,上方透气孔里漏下片纸,正落在他脚边。
捡起细看,是半幅舆图,用朱砂标着“宣府总兵府—紫禁城密道”。图角落款处,盖着与嘉靖御案相同的火漆印,却多了道极浅的划痕——像极了严嵩私印的残缺龙角。
“大人!蒙古遣使请和!”城外传来哨声。严楼望着手中舆图,忽然明白:嘉靖留他在宣府,不是查案,而是要用他手中的“错误标尺”,继续演这场火器戏码。
地道深处,枯骨怀中的《大明会典》又滑落一页。严楼瞥见,上面用密文写着:“弘治太子未薨,藏身……”字迹至此被虫蛀断,唯余个“严”字残笔。
雪,越下越急。严楼将舆图揣入袖中,指尖触到地道砖面的凹痕——那是个完整的龙形,与他在密室、火器、贡院所见的印记完全不同。
这才是真正的监国印记。而严嵩的龙形缺口,不过是皇室故意泄露的伪章。他忽然想起嘉靖烧掉的遗诏,想起“固皇权”三字,掌心的孔雀石碎屑突然硌得生疼。
当他踏出地道时,宣府城墙已换上明军旌旗。但严楼知道,这场胜利不过是假象。蒙古汗王退回草原时,必定带走了地道里的寒鸦暗纹——那是比佛郎机炮更危险的信号,暗示着京城中,还有未被拔除的“严”字党羽。
地道口,张顺忽然指着雪地:“师父,有人来过!”凌乱的脚印通向暗处,鞋印里嵌着极小的朱砂颗粒——与严嵩当日囚车旁的细沙,如出一辙。
严楼蹲下身,指尖划过雪地上的浅痕。那是个未完成的“严”字,最后一笔拖得老长,像极了滴血的刀刃。
他忽然抬头,望向紫禁城方向。漫天飞雪中,嘉靖的步辇正碾过西华门宫道。而在步辇阴影里,某个身影的袖口,正悄悄露出半片带龙形缺口的图纸——不是佛郎机炮,而是宣府密道的布防图。
第五十二章的钩子,藏在地道枯骨的《大明会典》残页里。那个未被虫蛀的“严”字残笔,暗示着弘治太子未薨,而藏身之处,或许与严嵩同姓同宗。当严楼发现这处线索时,即将面对的,不再是简单的舞弊案,而是关乎皇位正统的惊天秘辛——而嘉靖,很可能早就知道这个秘密,却一直用严嵩做幌子,掩盖真正的皇权威胁。
雪,覆盖了地道口的脚印。但严楼知道,下一场风暴,已在这漫天飞雪中悄然酝酿。那些藏在密道、火器、科举后的真相,终将像贵溪朱砂般,在历史的书页上,留下永远无法擦除的血痕。